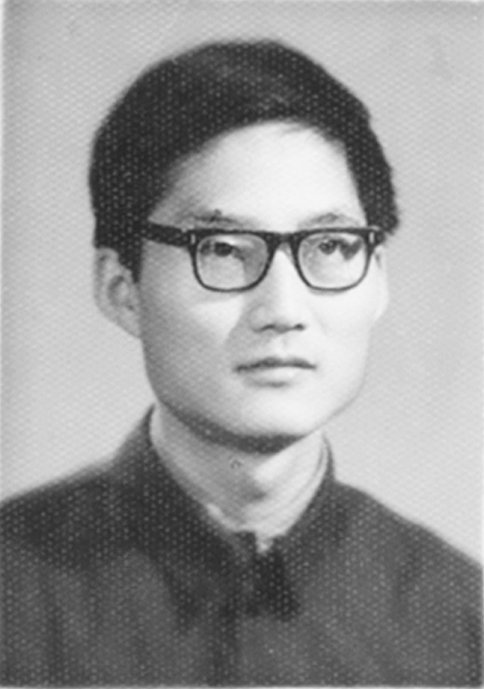
可以肯定地說,對于30年前參加過高考的人,那都是一段足以刻骨銘心的記憶。
從當時所具備的自身條件來看,我參加高考純屬偶然。1966年2月我和父親所在的研究所一起由北京來到西安,當時我上小學5年級。不過我很快發現,這里5年級學的和北京4年級的教學內容完全一樣。正當我準備跳到更高一年級求學的時候,所謂的“五·一六”通知把整個學校全攪亂了:高音喇叭取代了啷啷書聲,“紅寶書”取代了教材,溫良恭儉成了腐朽沒落的代名詞,取而代之的是“造反有理”的口號響徹學校的每一個角落。接著而來的,是“停課鬧革命”,是“革命的大串連”,是“消滅五分加綿羊,培養革命造反派”的教育改革…….對于一個只有十幾歲的孩子來說,面對這一切,又新鮮,又驚訝,又惶恐,當然也有點著急:時間一年又一年過去了,而自己的學業還停留在小學五年級。當然,這期間也有特別的收獲。一是糊里糊涂地從小學進入了中學,二是糊里糊涂地從中學進入到工廠。參加工作時我只有16歲多一點,當時的一個細節就讓我至今難忘:履歷表上有“學歷”一欄,我左思右想不知道該怎么填,于是跑回學校去問老師。老師倒是胸有成竹,十分干脆地告訴我:“初中,但是沒畢業”。
我參加高考也有著某些必然。這么說完全是出于那段特殊年代的特殊經歷。初次參加工作,肯定對什么都覺得新鮮,少不了會向周邊的人們問這問那,而且問得最多的一定是自己心目中最有威望的人。一次,廠里的一位技術員十分認真地對我說:你的學習精神不錯,最好能上大學。從那時起,我開始做夢,在夢中把自己和大學聯系在了一起。那個年代,上大學不用考試,主要是由組織推薦,于是我向組織提交了上學申請,但是石沉大海了。1973年,我聽到一個消息,說是當年的大學可以通過推薦和考試兩個渠道錄取。興奮的我覺得機會來了,再一次向組織遞交了申請,并眼睜睜地期盼著考試。結果,當年涌現出了一位“白卷先生”將我的大學夢徹底打碎了。當我一遍遍聽著電臺上介紹“白卷先生”的壯舉對中國教育發展具有的重要意義時,我發誓,決不再申請上這樣的大學,并決心要通過自學和這樣的大學較量一下。
對一個有工作壓力的人來說,自學談何容易。但是對一個被激怒了的人來說,又有什么困難不能克服呢!從那以后,我成了全廠唯一一個每天背著書包上班的人,一個再沒有節假日的人。在那個年代,一邊上班一邊讀書是件非常熬人的事情,考驗的不僅僅是人的智力,還包括人的體力和毅力;一邊上班一邊學習是件讓絕大多數人不能容忍的事情,聽到的不是鼓勵,而是冷嘲熱諷,風言風語。但是我始終沒有退縮,咬牙堅持,終于用了五年的時間自學完了初、高中的全部課程。當1977年深秋聽到恢復高考的消息時,我竟然哭了,就像一個受了很多委屈的孩子突然聽到了母親的呼喚。
我是1979年考入陜西師范大學的,學的是自己喜歡的漢語言文學專業。從工廠到大學,從工人到大學生,巨大的變化使我對大學里的一切都感到特別新鮮。
首先是同學之間的年齡相差特別大。當時的大學生絕大多數來自社會,應屆的高中生只占極少數。十幾歲的高中生和已到中年的社會學員同坐一個教室,除了給辨別誰是老師,誰是學生造成了困難,那兩代人同讀一本書的場面更著實有些滑稽。
其次是同學們的樸實。當時還沒有校服之說,可同學們的實際著裝卻像約定好了似的,男生幾乎全是四個口袋的中山裝,女生幾乎全是翻領的列寧裝。而且顏色也大體集中在青、灰、黑三種。記的新生報到后的第一次集合,站隊時我低頭看了一下大家的腳,發現全年級一百多人中只有我一個人穿的是皮鞋。
當然,給我留下更深刻印象的還是大學里的老師。時至今日,他們在課堂上的音容笑貌依然歷歷在目:霍松林先生那橫貫古今的淵博,高海夫先生那平靜語氣中蘊含著的深刻,暢廣元先生那激昂氣勢中時時流露出的睿智與膽識,馬家駿先生那將教學內容爛熟于心后所產生的超然境界,尤西林先生那侃侃而談中顯示出來的思辨力量……
最初,這些老師在我的眼里猶如一個個身懷絕技的廚師,能把每堂課內容處理得有滋有味,像美味佳肴一樣吸引著學生們的胃口。因此,每次上他們的課,我心里都會有一個從期盼到滿足,從滿足再到期盼的過程。后來,我把他們看成是蘊藏豐富的大山,除了外表郁郁蔥蔥,內里的涵養也十分豐富。他們是那樣平易,平易得每一個人都可以隨時走向他們;他們又是那樣深邃,深邃得使人一眼望不到頭。再到后來,我把他們看成是天上的星星,盡管距離遙遠,但是有一種靈光會時時在你身邊閃爍,失敗的時候可以給你鼓舞,成功的時候可以給你鞭策,迷茫的時候可以給你指引,消極的時候可以給你力量……
在不知不覺中,我從他們身上學會了讀書,學會了思考,也學會了做人,用了整整四年的時間完成了人生中的又一次質變。
記得有位作家說過:人生的道路是漫長的,但關鍵的時刻就那么幾步。的確,當30年的歲月彈指而過,回首往事,又怎么能不為自己當年邁出的那關鍵性的幾步而暗自慶幸呢。假如沒有當年那段如醉如癡的自學,我就沒有勇氣參加高考;假如沒有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我也不可能遇到那么多學高身正的老師;假如沒有這些師長的耳提面命,言傳身教,我也根本不可能使自己的人生軌跡沿著圣人們當年所設計的道路前行,走出了“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的生命曲線,并在這一過程中成就了事業,體驗了成功,悟到了人生真諦,而且,至今仍然能夠在自己設計的人生舞臺上無怨無悔地奮勇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