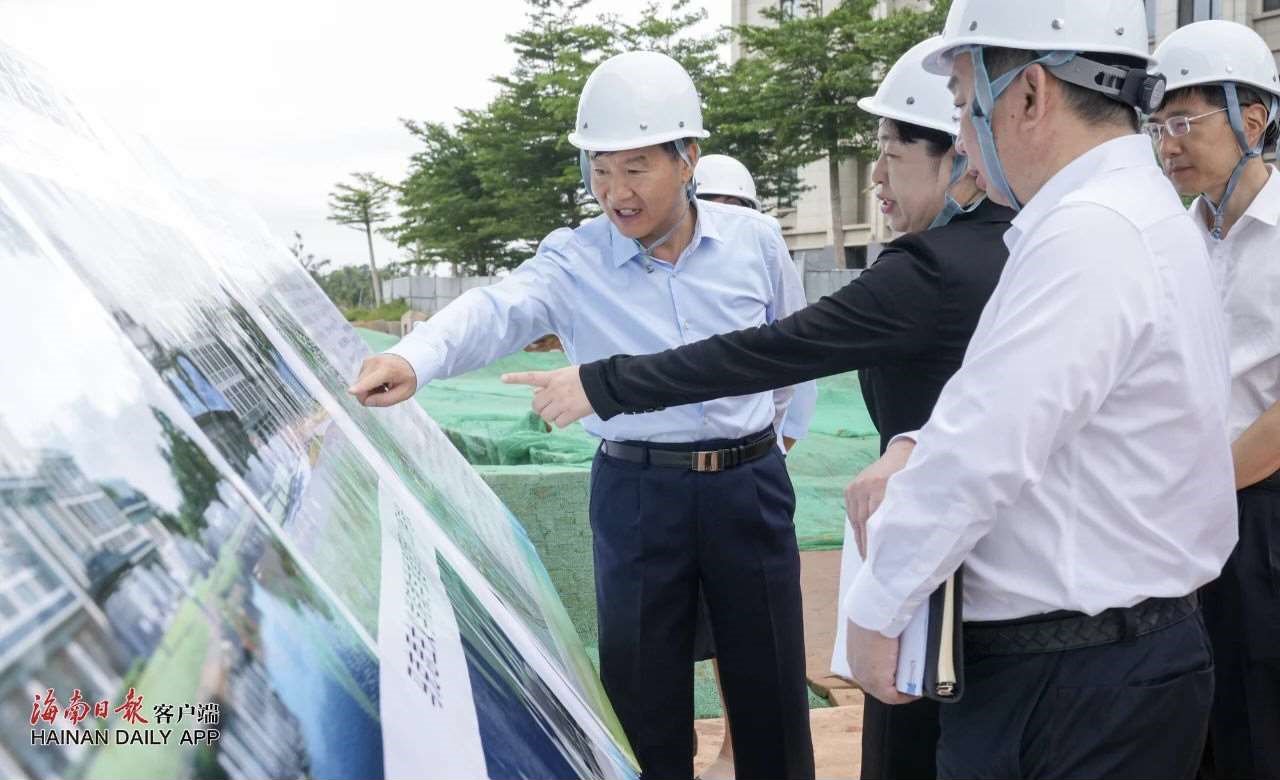“來遲了,來遲了!”老張笑著沖包廂里的人招了招手,回身把被雨淋濕的外套掛在衣架上,又悄悄用掛在那兒的另一件大衣蓋住了外套上一塊明顯的水漬。
“遲到得自罰三杯!”
“該罰!該罰!”
老張忙離開衣架找近處坐下,裝作無事發(fā)生。
這是大學(xué)畢業(yè)二十年的同學(xué)會,地點就定在學(xué)校旁邊。
兩杯酒下肚,老張的臉頰倏地?zé)饋怼K虼巴猓@里曾是城郊空地,現(xiàn)在建成了一條熙熙攘攘的步行街。周末的夜晚,大街上盡是鮮活的年輕人,連帶著這一塊的夜幕似乎都比其他地方亮堂一些。
對面坐著的人不依不饒地讓他喝完第三杯。老張忍住胃里的不適感,揚起笑臉沖對面的好哥們兒遙遙舉杯,又一飲而盡。老張?zhí)焐鷮凭荒褪埽@個人大概已經(jīng)忘了。
喊老張喝酒的人是他的上鋪劉希,也是老張學(xué)生時代的好哥們兒。兩人一起上課、吃飯、打開水,劉希給老張擋酒,老張就給劉希當(dāng)戀愛參謀。不想畢業(yè)一別,竟沒有再見過。
說沒有隔閡是假的。
老張在心里嘆口氣。今天可由不得他心生疏遠(yuǎn),他來這一趟,有正事要辦。
是臨出門前妻子千叮嚀萬囑咐“不準(zhǔn)由著性子胡來”“一定要拿下”的正事。
妻子肚里懷著第二胎,老張不敢惹妻子生氣。其實,往深里說,他一直對妻子很是歉疚。妻子讀書時是個美人,加上成績優(yōu)異,追求者眾多,卻偏偏看中了家世樣貌平平的老張。
“我喜歡你踏實肯干的勁兒。”她說。
這個女孩婚后并沒有過上寬裕的好日子,老張常常這樣想。抬頭看到妻子挪動著孕期龐大的身子操持家務(wù),心里便一陣難受。
酒過三巡,老張心跳如鼓,不敢再喝,便使出慣用伎倆,出門找服務(wù)員要了一聽雪碧。轉(zhuǎn)頭剛好看見劉希身邊坐著的同學(xué)打著酒嗝往衛(wèi)生間方向去了,立刻回身端起酒杯,閃身坐到劉希旁邊,扯了扯劉希的袖子,把他的眼睛從班花那個方向扯了回來。
“兄弟,我有件事想求你幫個忙。”老張壓低聲音。
“什么事?有話快說。”劉希不滿他打斷自己在女同學(xué)面前的表演,神情中有幾分不耐煩。
老張看得真切,一時不忿,想起妻子的話,又生生壓下去:“聽說哥們兒調(diào)進區(qū)實驗了,恭喜啊。”
“哈哈,碰運氣的,謝謝哥們兒啊。”劉希敷衍道,又轉(zhuǎn)頭看向班花的方向。老張不由得一起看過去,班花保養(yǎng)得真好,白膩膩的臉上一根細(xì)紋也沒有。
老張還是猶猶豫豫地開了口:“那個,兄弟,我女兒今年剛中考完,成績不是特別好……”
“成績不好,讀普高啊。”劉希埋頭吃菜,并不看他。
老張越發(fā)窘迫。
“兄弟,劉哥!”他左右看看,從褲兜里掏出一個牛皮紙信封,動作幅度壓到最小,“孩子自制力差,想讀個好點的學(xué)校,有好老師給管著,高考考個好點的本科。您給幫幫忙……”
劉希終于停下筷子,看了信封一眼,又看了看老張。老張飲酒后臉本就紅得厲害,此刻仿佛是在蒸騰了的熱氣中憋著。他稍微別開眼睛,擦了擦額頭上不存在的汗。
劉希再次夾了一筷子菜。
“哥們兒,不是我不愿幫你,現(xiàn)在制度嚴(yán)格,你分?jǐn)?shù)不夠就是不夠。”他看著老張如泄了氣的皮球一樣的神色,語氣又緩和下來,“我給你想想辦法啊,想想辦法。”
老張如蒙大赦,直起身子來想道謝,又想起了什么,忙把信封往劉希懷里塞。
“都是好兄弟,你這是做什么?”劉希輕聲斥責(zé),又把信封推回來。幾回合后,劉希勉為其難地收下了信封,聲音帶了懊惱:“跟我這么見外。”他端起酒杯:“來,咱哥倆再喝一個。”老張忙不迭地舉杯,心里好像有塊石頭落了地,卻又疙疙瘩瘩的,不得勁。
包廂里的冷氣開得足,老張打了個寒戰(zhàn),一下子清醒過來。
眼前是雙層鐵架床,木頭大桌子,頭頂?shù)男★L(fēng)扇吱呀吱呀,穿背心的室友窩在桌前吸溜泡面。角落里是一摞摞打包好的行李,地上散落著幾本舊書。
門被踹開,劉希頂著剛洗完還在滴水的頭發(fā)走進來,隨手拽開他的被子:“別睡了,一個午覺從1點睡到4點,我也是服了。”又朝吸溜泡面的室友笑罵道:“馬上要吃散伙飯了,你個沒出息的還吃泡面?”
“我餓了,你管我?”室友頂了一句,隔一會兒又說,“這算是咱班第一次同學(xué)聚會吧?真沒想到第一次就是最后一次。”
老張甩甩頭,這個夢充斥著連最老套的電視劇本都不愛寫的橋段,睡了一下午比醒著還累。
他從床上坐起來:“你懂什么,畢業(yè)之后吃的那才叫同學(xué)聚會,這頂多算同學(xué)聚餐。”又朝正在用毛巾粗魯?shù)夭潦妙^發(fā)的劉希踢了一腳:“今晚我破個酒戒,咱倆喝點。”
老張?zhí)麓玻瑢χ鴫ι系溺R子捋了捋頭發(fā)。鏡子里的少年意氣風(fēng)發(fā),和所有22歲的年輕人并無二致。
挨了一腳的劉希沖上來,兩人鬧作一團。頭發(fā)上未干的水甩在老張的T恤上,一塊明顯的水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