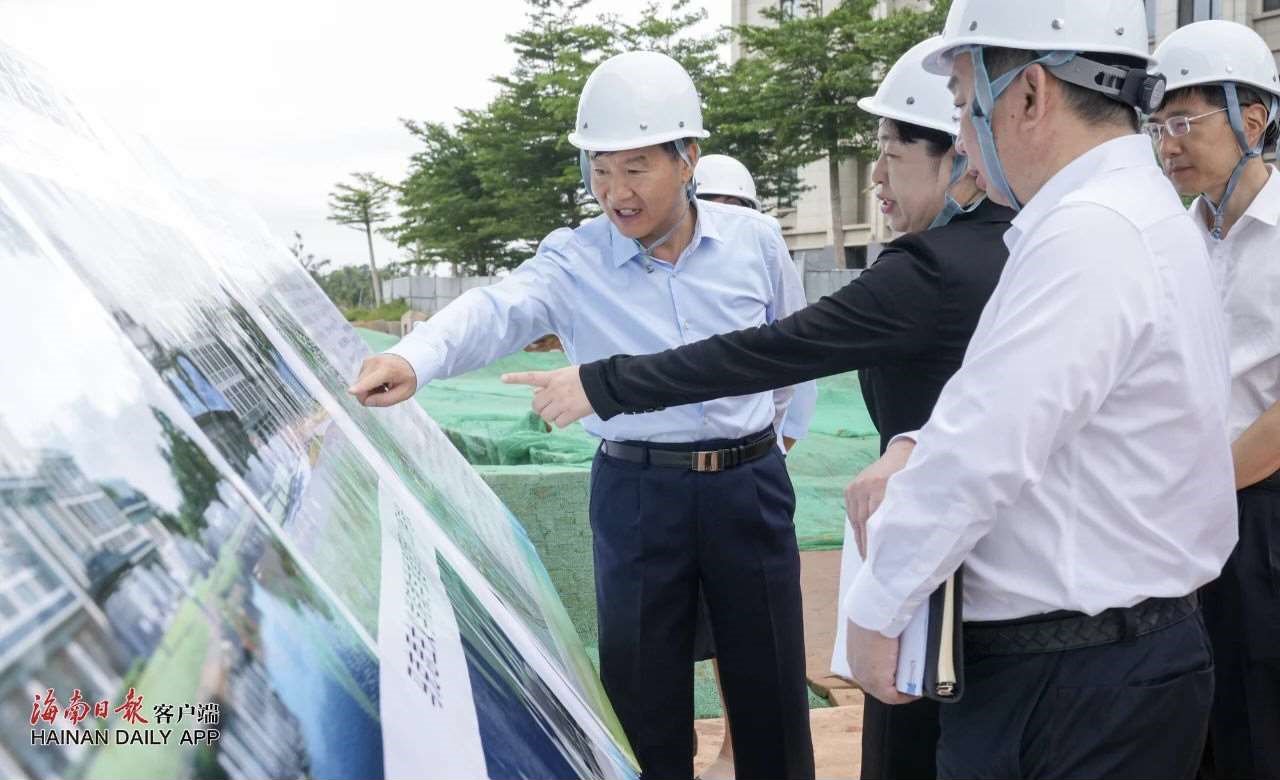“失火啦!快來救火啊!隨著陣陣敲碗擊盆的歇斯底里的呼喊,四鄉(xiāng)八鄰的鄉(xiāng)親們,從各處蜂擁而來。他們拿著臉盆水桶,接力棒似的從附近的水塘里拎著水桶相互傳遞,澆在著火的草屋上。梅香兩手各攬著弟弟妹妹的腦袋,驚恐之余輕輕拍打他們顫抖的雙肩,邊安慰他們別怕別怕。其實哪有不怕之理,農(nóng)村的房子一家挨著一家,中間只留有一條淌水的半米寬的水溝。七八十年代的房屋,一大半是土壘的墻面草蓋的頂。加上多日無雨的干燥天氣,很快,著火的阿風(fēng)家的三間茅屋,在眾人的匆忙搶救中還是化為一片火海。梅香家和阿鳳家是隔壁鄰居。
火勢逐漸減弱,有鄉(xiāng)親拎著水桶朝屋內(nèi)走去,隨著一聲驚呼,幾個膽大的立即跑過去在殘垣斷壁中,鄉(xiāng)鄰們看見女鄰居阿燒焦的尸體……
梅香的鄰居是一對地道農(nóng)民夫妻,男的村里人都叫他“大山”。梅香怎么也不明白,這個比梅香長一輩、黑不溜秋的皮膚加上一米六幾的個頭,還有點嘍背的男人,怎么就起了個“大山”的名號?跟村前的小山丘比,也比不上一圪。尤其是大山跟人說話時,盯著人看的一雙小眼睛,總是瞪得像隨時要掉出來一樣,人呢。梅香每次看見鄰居大山,總會哆嗦一下,想躲開,就被一聲呵斥,他媽的,不懂規(guī)矩的丫頭,不知道請教人啊!可憐的梅香畏畏縮縮站住,低低叫一聲“大大”。大山嘴里嘟嘟囔囔,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意,又用胳膊肘撞了一下梅香,走開了。鄰居的女主人阿鳳長得倒是白凈高挑,與她丈夫大山站在一起,簡直就是天鵝配癩蛤蟆。他們是怎樣結(jié)合在一起的呢?梅香聽母親說,阿鳳是隨她母親討飯到本村的,后來大山的父親看上了就尋思著,家里多添兩雙筷子兩碗飯,把她們母女倆留下,這樣,可以省了娶兒媳婦的錢。盡管當(dāng)時的阿鳳死活不同意嫁給大山,但她母親悲憫的懇求和眼淚還是讓她留下來了,家貧,吃不上飯,好死不如賴活著,沒法呀!
大山家扯了兩尺布,做了條新褲頭,算是給新娘的嫁妝,把阿鳳給娶回家。婚后幾年,阿風(fēng)的肚子不爭氣,連著生了三個女娃。在重男輕女思想嚴(yán)重的農(nóng)村,阿鳳的日子過得是多么不起頭。矮小的男人除了在身體需要發(fā)泄時親近阿鳳,其他時間,他們家是沒有一刻安寧的。不是打罵聲就是嚎啕大哭聲,大人哭了孩子嚎,此起彼伏。一開始,梅香母親忍不住還會去勸架拉架,可往往剛勸平息下來,回到家,隔壁鬼哭狼嚎聲又起。久而久之,鄉(xiāng)鄰們習(xí)慣了,路過的,偶爾進(jìn)去勸說幾句。嫌麻煩的,直接裝沒有聽見看見,徑直走過。之后,村里人都會看見阿風(fēng)核桃似的眼睛和臉上的五指印。好事的鄉(xiāng)鄰會忍不住對大山責(zé)備幾句,“人家千里迢迢來跟你過日子,你得好好待人家啊!”悶頭干活的大山要么一言不發(fā),要么眼珠子一,吐沫飛濺,“關(guān)你吊事!”此后,他家的事,鄉(xiāng)鄰不再過問。
連著好幾個日子了,梅香的母親沒有聽見隔壁吵罵聲,干活的鄉(xiāng)鄰們也看見大山脾氣出奇的好。有人忍不住問,“遇到啥好事了,咋人都變樣了,豬都睡炕了?大山嘿嘿一笑,露出一排大黃牙。
(二)
寒露到了,稻子黃澄澄的在田里彎著腰等待人們
的收割。都說一年到頭,就指望著到手的糧食收回去能賣個好價錢,讓家里大人小孩吃頓飽飽的米飯呢。田里人們忙得熱火朝天,天公也開始熱火朝天忙活開了,先是一陣風(fēng)帶來一大片烏云,隨之,豆大的雨點就哪里啪啦落下。忙著搶收的村民們更加賣力忙乎了。大家誰也沒有注意到大山今天競沒有上工,等到隊長點人頭分配工作時才發(fā)現(xiàn)。這可是破天荒啊!盡管大山脾氣暴躁,卻不曾偷過懶曠過工。這一家老小的吃喝還指望著他呢。一道閃電,劃破半邊天,雨越下越大,大伙只能把割好的稻把堆在一起,用薄膜蓋住。雨珠噼里啪啦砸向大地,人還沒有進(jìn)村,衣服都濕透了。
梅香的母親拾了一塊破薄膜,用雙手擎著遮在頭頂擋雨。跑過大山家門前時,習(xí)慣性瞥了一眼,看見阿鳳手里抱著孩子在輕拍搖晃。梅香的母親抬不起腳步,定定地站在那愣了愣,阿鳳看見有人在看她,忙別過臉去,不作理睬。她的這副模樣,梅香的母親已經(jīng)習(xí)慣了。從她進(jìn)了這個村莊進(jìn)了這個家,阿風(fēng)就沒有與任何人多說過話,除了嗯,或者點頭,還有,挨打時的嚎哭。
好長一段時間了,隔壁家一直安安靜靜的。一次梅香和母親去鎮(zhèn)上回來,正好遇見阿鳳家的老大老二在路邊玩,梅香母親從褲兜里摸出一顆糖,在她們姐妹倆面前晃了晃,想吃嗎?倆娃相互望了一眼,咽了咽口水,不做聲,梅香母親用牙咯嘣一聲,把一顆糖咬成兩半,一娃口里塞一半,娃把半顆糖含在嘴里,慢慢地吮吸著。她們已經(jīng)不知道啥時候嘗過糖果甜蜜的滋味了。梅香母親看見心里很不是滋味,沒有辦法,誰家都不富裕呀,能把肚子填飽,餓不死,就已經(jīng)阿彌陀佛了。倆娃倒是懂事,糖果甜蜜的滋味浸潤了她們的細(xì)胞,整個人跟著甜蜜起來,露出難得一見的好看的笑容:“謝謝大媽媽。”梅香母親一手拉一個娃的小手,“你媽抱著的寶寶是小妹嗎?現(xiàn)在咋沒有以前哭鬧得兇了呀?你們爸爸脾氣也好了不少,不像以前那樣打罵你們了嘛。笑容在姐妹倆的臉上瞬間凝固,倆娃把頭垂下,終究忍不住,大丫頭哇的一聲哭了起來,緊跟著二丫頭也抽泣起來。梅香母親趕緊摟著她倆安慰說,“別怕別哭,告訴大媽媽,媽媽抱著的是不是小妹?”“小妹被爸爸送人了,換一個弟弟回來了。”倆姐妹的話驗證了梅香母親的猜想。一次路過,看見阿鳳在把孩子尿尿,她看見一泡尿尿得好遠(yuǎn),心想,這女娃咋尿那么遠(yuǎn)?等她靠近時,阿鳳已經(jīng)把孩子尿布給兜了起來。現(xiàn)在想來,可真把三丫頭給換人了。梅香母親深深嘆了口氣。天空有飛鳥越過,嘰嘰喳喳,它們是自由的。紙終究包不住火,換娃的事情很快在周邊傳開了。村里鄉(xiāng)里的干部三番幾次上門做思想工作。可不是被大山罵跑,就是被阿鳳哭哭啼啼聲給感化,來的人都搖搖頭,走了。換娃的事情,在那個年代的貧窮鄉(xiāng)村是見怪不怪的。
男娃的回來,阿鳳的地位顯然提高了一點。她已經(jīng)不再是往日大山非打即罵的主了,甚至能聽見她與大山的互罵。
(三)
冬天,麥子錐上了肥,地里的農(nóng)活已經(jīng)做完,村上安排每戶出一份勞力去十里之外的四圩挖河挑塘。梅香父親及大山和鄉(xiāng)親們在一個大早上,就被拖拉機連同棉被扁擔(dān)一起拖走了。村上的女人們站在村頭,在冒著白煙的突突聲中,目送男人們出工去了。這個冬天,應(yīng)該是清冷的吧。女人們搓著布滿老繭的雙手,哈著熱氣有一句沒一句閑搭著。
冬日的農(nóng)村最是清閑,孩子們也放寒假了,大人們沒有必要像以前那樣,天麻麻亮就起來做早飯干農(nóng)活。躲在暖被窩里哪怕多賴床一會也是幸福的事情。這天,天還沒有亮,梅香母親肚子咕咕鬧個不停,估計是受凍了。茅廁在外面,打開大門,跑幾米遠(yuǎn)就到了,燈都不需要點上。她披了件棉衣,輕輕拉開大門,不能驚醒了孩子們的睡眠。她快步走向茅廁,褲子剛解下,就稀里嘩啦一陣排山倒海,肚子一陣絞痛后,蹲著休息了一會,感覺好多了。鄉(xiāng)下人,不矯情,什么苦什么痛沒有經(jīng)歷過?這點拉稀算個球。梅香母親拉起褲子,把披著的棉衣往肩上送了送,就在她跨出茅房準(zhǔn)備跑進(jìn)家門的那一刻,眼前一道人影差點與她撞了個滿懷,這可把她嚇得半死,還沒有等她緩回過神看清楚是誰,那人快速沖向前方,消失在薄霧中。隔壁阿鳳家窗前黯淡的燈光也熄滅了。
村莊在雞鳴狗叫聲中蘇醒了,各家煙筒里陸續(xù)冒
起了白煙。淡淡的薄霧在晨曦中散開,陽光輕柔地吻著萬物。梅香的母親經(jīng)過下半夜的肚疼和驚嚇,回去一時也沒有睡著,那個匆匆一閃而過的身影是誰呢?三更半夜的又去哪里呢?按理說,村上留下的男人,除了上學(xué)的孩童,要么是七老八十的風(fēng)燭老人,要么就是殘疾腿廢的兔二叔。老人走路都不穩(wěn)的,哪有那么快的速度奔跑?那個兔二叔,是村東邊的光棍漢,因為年輕時與人打架,腿被人用鐵鍬給砸傷,又因為條件有限,沒有及時治療,落得個“鐵拐李”的稱號。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怎么可能跑那么快?梅香母親把留在村里的男人們都在腦海里挨個篩了一遍,就是想不出那個人是誰,還有那熄滅的油燈,難道是巧合?在迷迷糊糊的回籠覺中,梅香的母親隱約聽見有人把門拍得啪啪響。拉開窗布簾一看,天已大亮。梅香母親趕緊披衣下床,打著哈欠拉開門栓,是隊長。隊長不是跟隨村里男人們?nèi)プ龉ち寺?咋回來了?見梅香母親愣著,高個的隊長瞪了梅香母親一眼,不認(rèn)識啦,瞅著我?“哦哦,你不是隨他們出工了嘛,咋回來了?”“哦,是的,大伙出去的匆忙,有人衣服帶少了,有人棉被帶薄了,冷,所以,我就和開拖拉機的王老頭回來一趟,幫大伙捎點東西。你看,你家還有需要我?guī)н^去的東西沒?這要到年底才回來,還要一個多月的時間呢。對了,你家男人說要幫帶一條煙去,家里有嗎?沒有你就去買,我下午走。”隊長說完,對屋里瞅了兩眼,娃都沒有起來啊?”“嗯吶,都賴被窩里面呢,這不我也才剛起來,早飯還沒有燒呢。”男人不在家,晚上早點關(guān)門睡覺,不要胡思亂想睡不著啊!”臨走,隊長揄揶著說。隊長走后,梅香母親愣愣地站了一會,也沒有過多時間回味隊長話里的意思。她忙著把櫥柜里的那件厚棉衣抽出來,又翻看了一會,感覺實在沒有什么要帶上的,出門去鄉(xiāng)里供銷社買了五包“大前門”和兩包“飛馬牌香煙。摸摸褲兜還剩兩塊錢,又稱了五角錢葵花籽。男人嘛,是家里頂梁柱,伺候好了,一家老小少挨餓受凍。自己在家?guī)?即使沒有錢買菜,起碼菜地里面的青菜蘿卜是管飽呢。
在回來的半路,梅香母親遇到了王老頭。說是王老頭,其實才四十出頭的壯實漢子,長得五大三粗的,因為父母去世早,幼年頭上長癩子,沒有錢治療,年紀(jì)輕輕就是一幅禿頂?shù)哪?像個老頭。盡管頭腦活絡(luò),能吃苦,肯學(xué)習(xí),第一個報名學(xué)習(xí)開拖拉機,因為家貧,至今還是光棍一個,聽說與鄰村的張寡婦有牽扯。也時常看見他干公家活的時候捎帶幫張寡婦帶點東西去鄉(xiāng)里賣了換錢。大家心知肚明,只是不說破而已。梅香母親看見王老頭一個人扛著一個蛇皮袋,盡管冬天,還是看見他額頭細(xì)微的汗珠。梅香母親老遠(yuǎn)就招呼,“王老弟,你這是干嘛去呢?”“哦哦,家里雜什,賣了去供銷社換點鹽糖。”王老頭說著話腳步卻沒有停下。梅香母親看王老頭走遠(yuǎn),才扭頭朝家走去。
(四)
進(jìn)了臘月門了,家家戶戶該忙著置辦年貨了。殺豬是村民們最值得期盼的大事。經(jīng)過兩個多月的體力勞作,挖河回來的男人們早就饑腸轆轆,期待隊里早點將養(yǎng)的膘肥體壯的兩頭大豬殺了,好犒勞一冬的腸胃。一大早,在村長的指揮下,婦女們早早燒好了幾大鍋滾開的水,備好了捆豬繩,就等殺豬的人來。太陽已經(jīng)升起了三尺高,殺豬水熱了冷,冷了又燒,快午時分,派去請殺豬的人領(lǐng)著殺豬的周屠夫才哼哧哼哧抬著木盆過來。村里男女老少,此刻就跟迎接一個盛大的活動一樣,走出家門,就連平日很少出門的阿鳳,也抱著那個換來的男娃,首次公開拋頭露臉出現(xiàn)在眾人堆里看熱鬧。或許出門少的緣故,亦或從不下田的因由,一副天生的美人胚子的阿鳳,站在嘰嘰喳喳的人群里,是那樣的顯眼,那樣的與眾不同。村里男人的眼光總是有意無意在她臉上游走,可惜身上穿著厚棉衣,凹凸有致的曲線只能憑那些男人去想象了。周屠夫是附近幾個村子僅有的會殺豬的,尤其是在臘月的好日子里,更是忙得天不亮就出門,天黑透了才回家,酬勞就是別村殺豬給個幾斤豬肉,拎回村燒了,叫上村長和村里幾個干活得力的過來打打牙祭。
周屠夫不愧是個殺豬的好把式,一刀下去,干凈利落,沒等豬嚎第二聲,就見血柱“撲哧”一下,從豬脖子處噴天而射,被男人們分別壓住的四個豬腳,奮力掙扎了幾下,肥胖的身體抽搐了一會。終于,兩腿一蹬,不動了。后面刮豬毛,開膛破肚等一系列細(xì)致活做得讓鄉(xiāng)鄰們嘖嘖贊嘆。阿鳳看著,眼睛也亮起來。周屠夫走南闖
北,啥人啥場面沒有見過,他在這一群被風(fēng)吹得皮膚粗糙的村婦里面,早就發(fā)現(xiàn)與眾不同的阿鳳了。只是人多,不敢過分造次。但眼角的余光總是會瞄向阿鳳這邊。村長按照每家每戶的人頭,進(jìn)行年終分肉,肥瘦都搭一點。大山縮著脖子,操著雙手,瞪著雙眼,瞅著周屠夫和隊長在分肉。“大山,這是你家的。”當(dāng)隊長點到大山名字時,大山擠近案板跟前,用手拎起一掛略微顯瘦的五花肉,左右上下瞅了又瞅,隨后“啪”的一聲,扔在門板上,“欺負(fù)人吶,啊!一點油水都沒有的,盡是瘦肉,誰要誰拿去,我不要,當(dāng)我好欺負(fù)啊!”大山雙手抱胸,吐沫星子直噴周屠夫。他還是有點畏懼隊長的。阿鳳一手抱娃一手上前準(zhǔn)備將大山拉走,可大山像腳下生了根,就是拽不動,還回頭用他那大白眼珠子瞪她。周屠夫望望面帶慍色的村長,又看看手足無措的阿鳳,手起刀落,油晃晃的三斤大肥膘看得大伙眼饞。周屠夫直接走到阿鳳面前,半空晃蕩著。大山一把伸手奪過,生怕被人搶了似的直奔家去。阿鳳抬頭,對上周屠夫盯著她的眼,臉?biāo)⒌赝t,抱著娃匆匆回家了。“你小子是不是有小心思啊!把那么好的肥膘給那娘們家了啊?”等阿鳳離開,有人立即拿周屠夫開涮,反正閑著沒事。大伙在嘻嘻哈哈的調(diào)侃中散去。場地上有幾只雞和貓狗在舔舐剩余的殘渣,不時為爭食而鬧得雞飛狗跳貓兒叫。中午的炊煙已經(jīng)升起,有香味彌漫,整個村莊沉浸在一片太平盛世的歡樂年華中。
當(dāng)一張四方桌晃晃蕩蕩出現(xiàn)在梅香家門前時,梅香父親忙丟下手中正在搗鼓的鐵鍬,蹲下身子,一看,是大山。此刻的大山半蹲在桌肚子底下,雙肩扛著桌子,滿臉通紅,罵罵咧咧,滿嘴的酒氣沖天。他發(fā)酒瘋了。梅香父親拖住桌子,大喊著“出來”。可桌下的大山就是不出來,趁著梅香父親緩氣的當(dāng)口,猛一起身,扛著桌子跑遠(yuǎn)了。一群孩子跟在后面跑,吵吵鬧鬧唱著跳著追著。村民們趁著午后的好陽光,聚在一起抽煙聊天曬太陽。也不再過問大山酒鬼的鬧騰了,由他去鬧吧,爛泥巴扶不上墻的一坨屎。
兩個十二三歲的孩子喘著粗氣,跑進(jìn)聊天的人群,結(jié)結(jié)巴巴說:“不好了,酒鬼大山扛著桌子滾西頭水塘里面去了。”等眾人七手八腳把大山拉上岸的時候,大山只見出氣沒見進(jìn)氣。也是巧,這水塘是去年冬天剛挖的,為了夏季多儲雨水灌溉莊稼,就特地挖深了些。今年夏天雨水多,整個塘水還是很滿的。大山是會游泳的,換做平時,是淹不死的。估計是酒多的原因,扛著桌子也看不見,跌落水里,等孩子叫來大人,閻王已經(jīng)搶先一步在等他了。盡管鄉(xiāng)親們采用了用老牛駝背壓水的方式,還是無回天之力把大山的命搶回來。阿鳳領(lǐng)著三娃,哭得昏天黑地,家里頂梁柱倒了,這往后的日子咋過呀。眾人也免不了陪著落淚。盡管平日不待見,此刻,淳樸善良的村人還是幫襯著料理了大山的后事。
(五)
在守著大山“六七”后,開春了,阿鳳收拾好自己。她一改以往閉門家中坐的姿態(tài),換上大山的粗衫糟褲,讓大丫二丫帶著小娃,自己跟著村里的婦女們一起出工去了。本以為肩不能挑擔(dān),手不會提籃的阿鳳,在隊里干活一定是落最后的。哪知道,她挖起墑溝溝來,雖慢了些,但又深又直。第一次出工,就顛覆了她在村里人腦海里以往的印象。原來,她竟是個莊稼好把式啊!
又到了“手把青秧插滿田”的季節(jié),天氣漸漸暖和起來。大人小孩在家度過了安逸的農(nóng)閑時光,布谷鳥不停召喚著勤勞的人們快點耕種。一片白汪汪的水田,看起來就讓人害怕,田埂邊的村婦們嘰嘰喳喳邊嘀咕著,邊卷起褲腳,試探著下水。五月天,還冷著,赤腳下水田,最容易凍感冒的。可季節(jié)不等人,時間不等人啊!“咦,誰已經(jīng)下田了?”大伙仔細(xì)看,才看清楚是阿鳳。阿鳳默不作聲,已赤腳蹬到了田埂最里頭,要拖秧繩呢。大家不再嘰嘰喳喳了,誰想輸給一個不見做過農(nóng)活的寡婦呢,那不被人笑掉大牙?插秧在農(nóng)村最是考驗一個人的農(nóng)活如何了,都在同一個起跑線上,一同插秧,比的是速度和干勁。速度跟不上,會被周圍的人插的秧給包圍起來。直起身子,回頭看,就自己屁股后面一片白汪汪的,人家已經(jīng)是綠油油一片,沒有言語的奚落,自己看著就會羞愧難當(dāng)。這一群女人心知肚明,在一起忙活那么多年,誰不知道誰的底子,但今天阿鳳是第一次下田插秧,沒有人知道她的插秧速度如何。所以一開始,大家還是不敢懈怠,隊長老婆阿蘭粗著嗓門喊,“阿鳳第一次下田,就讓她在最邊上插吧。”在邊上插秧,
般是留給剛嫁進(jìn)村的小媳婦或者手腳不利索的位置,這樣,即使插慢了,不至于被人家圍堵在里面,成一盤死棋好看。阿風(fēng)是什么把式,一次就能看出了。
水田是鏡子,映照著藍(lán)天,映照著白云。農(nóng)婦們在插秧,把秧苗插在了藍(lán)天上,把秧苗也插在了白云上。空中的鳥兒跟忙碌的人們一樣,來來往往盤旋飛翔鳴叫。不知道什么時候,田埂邊站著幾個挑秧的漢子,他們放下扁擔(dān),立在那,對著秧田指指點點。偶爾傳來的說話聲,驚動了田里埋頭插秧的婦女們。此刻,有人趁直腰的空當(dāng),往兩邊瞅了眼。發(fā)現(xiàn)最快的居然是阿。阿鳳插秧快不打緊,關(guān)鍵她這個木拙子,竟不知道這么做事不顧及其他人的臉面,她只是一個勁地埋頭插秧,后退的步子輕盈快速,完全沒有其他人的那種艱難、疲憊。有人小聲嘀咕著,隊長老婆也發(fā)現(xiàn)了情況,這可不是她釋放的大度所希望得到的效果。她臉立即黑下來,要論插秧快,在生產(chǎn)隊,誰不知道她阿蘭是個快手?大家是不是讓著她,另當(dāng)別論,但她一直擔(dān)當(dāng)著這個光榮的頭銜。本以為,今天給阿鳳一個機會,讓她知道她是在照顧她的,也讓大伙知道她阿蘭是菩薩心腸。誰知道這個不開竅的貨,居然讓她,不,是讓大伙出丑。這還得了!人長得騷就算了,還要用干活來吸引男人的目光。阿蘭越想越氣,索性扔下手中的秧苗,大聲嚷嚷:“阿鳳,你既然這么快,來來來,你年輕,身手好,你以后就在最里面插秧啊,我們都老胳膊老腿了,趕不上你,你就能者多勞哈。”大家一起跟著哈哈。阿鳳不做聲,繼續(xù)埋頭將這一隴插到頭。她回頭想去幫忙,卻不知道怎么下手,不,是不知道怎么插腳進(jìn)去。這時的阿蘭,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愚笨。可是,癤子的傷疤已經(jīng)揭開,只能讓時間去慢慢癥愈。阿蘭相信,大伙會明白自己不是存心的。
有了阿蘭這個插秧快手的加入,生產(chǎn)隊里六七十畝的秧田,以前最快也要八天才勉強插完,現(xiàn)在提前了一天,大家還早早收工。廣播通知,晚飯后,大伙去隊長家里開個會。
人們陸續(xù)來到隊長家,隊長在挨個點名的時候,發(fā)現(xiàn)阿鳳還沒有來。隊長老婆阿蘭立即囔囔,“擺什么臭架子啊,開會還要人去抬不成……”話音未落,阿鳳走路像企鵝般出現(xiàn)在門口,阿蘭的下半句話硬生生被隊長瞪著的大白眼給噎下去了。會上,隊長就農(nóng)忙季節(jié),針對各家表現(xiàn)給予了點評,當(dāng)然,以表揚居多。畢竟,大伙辛苦一季了,筷子伸出來還有長短呢,人怎么可能沒有個先后快慢?末了,隊長瞅了眼一直沒有說話的阿風(fēng),“今天,我要著重表揚阿鳳,雖說來我們村有幾個年頭了,但今年還是第一年參與集體勞動,而且表現(xiàn)很積極,值得大伙學(xué)習(xí)。希望大家互相幫襯著,她有不會或不懂的,其他老娘們多教教帶帶啊。”隊長話音未落,肥胖的阿珍就陰陽怪氣說道:“隊長,你太小看人家了,人家哪樣兒不會,要我們幫襯?我們還得靠她幫襯著呢,別讓我們把老臉都丟在山圪垃里面,快沒有臉回來見人了。”“你這是說的什么話啊!”隊長虎著臉瞪了阿珍一眼,“哦,就興你們干活搶在前頭,就不能讓人家超過你們?那這樣以后你們干活多了就不要在我面前訴苦告狀詆毀別人。真是的,看不得別人做事落后,也嫉妒別人在前,怎么伺候你們才開心?”隊長一通發(fā)火,把后面幾個想嘮叨的也給擋了回去。“散會!”
“阿風(fēng),你等一下。”隊長叫住走出門口的阿風(fēng),屋里,阿蘭的眼睛要噴出火來。“你呢,現(xiàn)在一個人也挺不容易的,還得要照顧三個年幼的娃,這樣吧,農(nóng)忙過了,農(nóng)活暫時也告一段落,你明天開始,早田和山上種豆子種花生之類的你就不要去了,把生產(chǎn)隊的一群鵝和兩頭牛跟小虎子一起照看好,這樣,你也順便把小兒帶身邊,讓倆閨女去上學(xué),不能誤了孩子的學(xué)習(xí)。”
夜晚的鄉(xiāng)村一片漆黑,阿鳳的眼淚亮晶晶的,在夜空下滑落。她朝隊長鞠了個躬,想表達(dá)點什么,可瞅著隊長身后阿蘭的目光,還是啥也沒有說,轉(zhuǎn)身離開了。
(六)
在那個按勞力掙工分的年代,工分的多少直接影響分配糧食的多少。家里勞力越多,糧食會分得越多。阿風(fēng)家的勞力就她一人,公婆一個瘸子一個瞎子,隊里照顧只給兩老人三分之一的工分,勉強他們糊口。家里三個娃不大,但也是三張嘴啊,是嘴就得要吃飯。望著米缸里的米在逐漸下沉,阿臉上布滿了愁云。大人可以勒緊褲帶,可孩子還小,長身體呢,咋能虧待?夜深了,昏暗的煤油燈下,阿鳳納著鞋底望著熟睡的娃,深
深嘆了口氣,眼神迷離。“咚…咚有人在敲門,阿鳳回過神來,敲門聲消失了。她愣了一會,自己走神聽錯了吧。她把煤油燈芯挑了下,屋里一下子亮堂起來,她埋頭繼續(xù)納鞋底。“咚咚”敲門聲又響,這次她沒有聽錯,這個時候,會有誰來敲門?阿風(fēng)有點害怕,端起煤油燈,一手?jǐn)n著燈火,防止火被風(fēng)吹滅,家里的火柴也剩不了幾根,省著擦呢。她來到堂屋門口,并沒有急著去打開門栓,只是低聲問:“誰?”“我。”像是隊長的聲音,阿鳳又問了一句,確認(rèn)是隊長,猶豫了一下,放下油燈,輕輕拉開門栓,剛打開門一條縫,隊長閃了進(jìn)來,隨他身子進(jìn)來的,還有背后小半口袋米。
有了隊長的特殊“關(guān)照”,阿風(fēng)不再為生計發(fā)愁了。她的農(nóng)活也因為寡婦的身份而被優(yōu)待。這惹得那群好事的婆娘們更是妒火中燒,可又無可奈何,只是,阿鳳在村里好像又回到了從前那樣,與其他人孤立起來,除了男人們。
梅香的母親曾看見賣貨郎的也從阿鳳家里出來,碰見了,還沒有問,阿鳳就急忙解釋說人家過來討口水喝的。阿鳳家門口出現(xiàn)陌生男人的身影逐漸多了,村里的,鄰村的也有。雨天,大伙都出不了工,都閑在家里,女人們忙用碎布拼做護(hù)袖圍裙和孩子們的書包,或者納著鞋底,男人們在家躺著養(yǎng)養(yǎng)精神,再閑不住的,就串門閑聊打撲克。梅雨天,是最適合有故事滋生的。
梅雨天,滋生了故事,也滋生了疾病。阿鳳有兩天沒有出工了。盡管天已放晴,盡管隊長給她的事情只是看牛放鵝,但她還是沒有出現(xiàn)在野外,她躺在床上,面部痛苦的表情讓人看了揪心。梅香陪著母親踏進(jìn)阿鳳家房間時,一股酸臭味撲鼻而來。兩個女娃渾身臟兮兮地坐在門檻上寫作業(yè),小男孩在床上睡著了,滿臉鼻涕。糞桶里面的糞便不知道有幾天沒有倒了。六月頭,天已經(jīng)熱了,蛆蟲蠕動著軟綿綿的軀體,爬滿糞桶周圍。梅香不敢進(jìn)去,她退出來,站在堂屋,桌子上面有昨晚上吃剩的米飯,有蒼蠅在飛舞。一碗咸菜被扒的掉落在桌子上,一只雞跳上桌子,邊啄食邊屁股一撅,拉出一坨屎……梅香呆呆地站著看著,兩女娃,瞪著兩雙大眼睛無神地盯著梅香。蠟黃的臉上沒有一點孩子應(yīng)有的生氣。“你這是咋啦?哪里不舒服?”梅香聽見母親在問阿鳳,語氣里滿是擔(dān)心。“哎,我咋開口呢?”良久,聽不見阿鳳回答。“你不說,我怎么能幫到你呢?”“去衛(wèi)生院看了,說是婦女病,也拿藥涂了,沒有用,就是疼,難受。”阿風(fēng)有氣無力地斷斷續(xù)續(xù)地回答后,是良久的沉默。
天,已經(jīng)暗了下來,梅香跨出門口,看見西邊晚霞火一樣燒著,紅彤彤的,像萬丈光芒,要穿透一切似的。可畢竟是夕陽,再烈艷,也力不從心,無法穿透阻擋她的浮云。漸漸地,黑暗籠罩了四周。星星眨巴著詭異的眼睛窺視著大地,村莊靜悄悄的,偶有幾聲犬吠,讓人毫不設(shè)防從睡夢中驚醒。
(七)
阿鳳得了性病,村里像炸開了鍋。白天有女人站在她家門前破口大罵,什么難聽罵什么。晚上,即使半夜,門也會被磚頭砸得咚咚響。屋里睡熟的孩子會被嚇得哇哇大哭。整個村莊籠罩在一片驚悚中。
一陣大火升騰后,將阿鳳帶走了,被澆滅的大火也熄滅了村里人心頭的怒火。村莊很快恢復(fù)了以往的寧靜。阿風(fēng)被換回來的男孩,還是被生父母領(lǐng)走,兩個女娃分別被親戚領(lǐng)養(yǎng)。
梅香長大出嫁后,每每回娘家,路過曾經(jīng)的阿鳳家的位置,都會佇立良久。阿鳳的家被大火燒光后,隊里并沒有沒收這個老宅基地,而是找人在原來的舊址上簡單修繕了一下。沒有人住歸沒有人住,孩子以后還得認(rèn)祖歸宗的呀。
經(jīng)年后,阿家破舊的草屋不見了,兩層高的小洋樓平地拔起,紅彤彤的琉璃瓦,白花花的墻壁,在這個小村落顯得熠熠生輝。阿鳳的大閨女小琴幾次回村后,出資把村里的疙瘩路買了石子鋪平。村里老一輩人,尤其是曾經(jīng)詛咒過小琴母親的老女人,已經(jīng)是走路都撐拐棍了,走在小琴出資鋪平的路上,雙腿顫巍巍的,心,也跟著顫巍巍的。那個該死的年代那個該死的已經(jīng)死了的,都統(tǒng)統(tǒng)忘記吧。可能忘記嗎?這丫頭長得越來越像阿了。一滴滴的濁淚,縱橫流淌在布滿褶皺的臉上。
村莊的上空,炊煙升起,裊裊的,與晚霞相融,燃燒西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