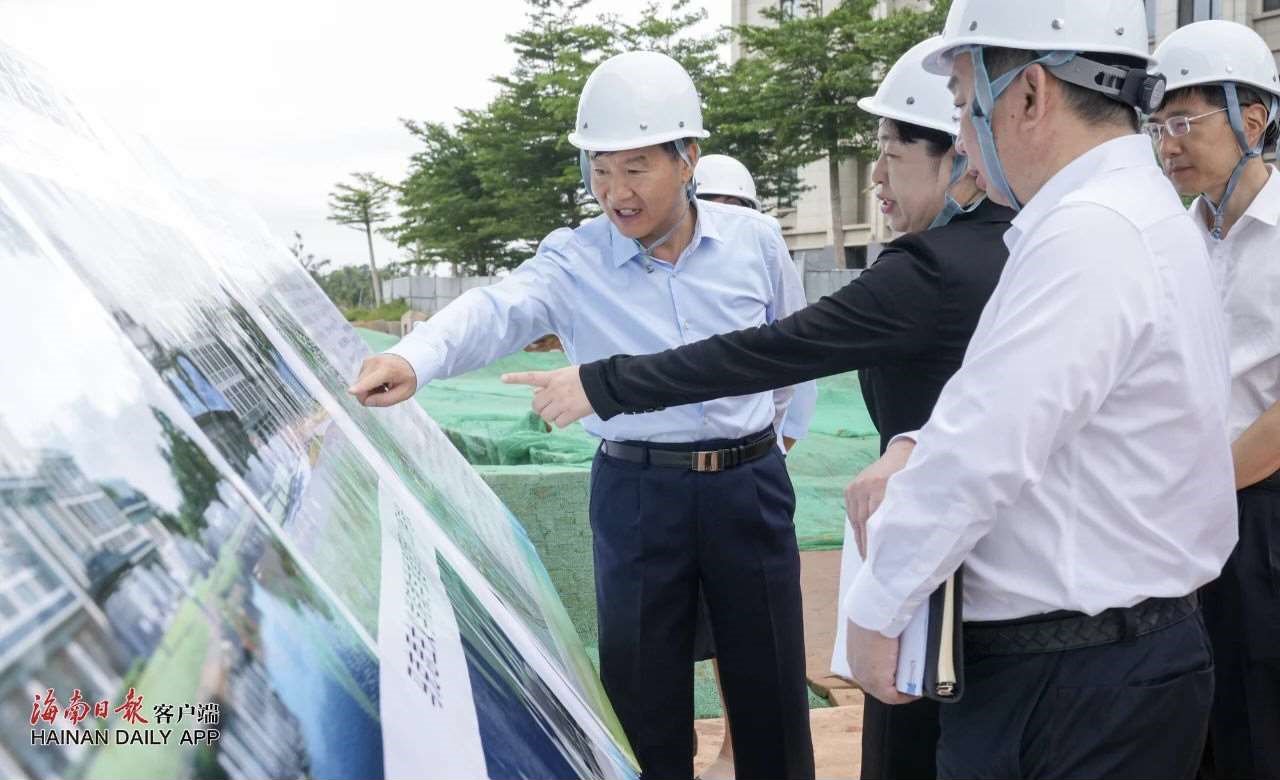五月的麥田
“鼓鼓翅子紅一遍,下來麥子吃涼面;鼓鼓翅子紅兩遍,下來黍子吃炒面;鼓鼓翅子紅三遍,下來谷子吃干飯……”
我坐在從長清開往市里的班車上,冷氣開得很足,密封的空間卻還是讓人覺得憋悶。昏昏欲睡中忽聽得鄰座的一位老師說:“看!麥子黃了!”我瞥向窗外,不遠處有一大片麥田正泛著金黃色的波浪隨風起舞,一輛閃著白光的火車正從麥浪中急速穿過,好似銀龍一般。上下班天天從這里經過,竟沒有發現原來這里有一塊麥田。很快,這片麥田被班車遠遠地甩在了后面……“鼓鼓翅子紅一遍,下來麥子吃涼面,鼓鼓翅子紅兩遍,下來黍子吃炒面,鼓鼓翅子紅三遍,下來谷子吃干飯……”這首古老的小調,在老家人人耳熟能詳,卻應景地反映著農事。“鼓鼓翅子”是指的臭椿的果實,那一串串長著翅膀的小家伙會紅了又綠,綠了又紅,如此這般反復三次就到了深秋。而適時出現在臭椿樹上“咕咕、咕咕”唱歌的鳥兒,到現在我也不敢確定是不是“戴勝鳥”。在故鄉,人們干脆把這頭上插著一把打開的折扇般美麗的鳥兒也稱為“鼓鼓翅子鳥”。當“鼓鼓翅子”第一遍悄悄變紅的時候,簌簌的棗花也開始灑落一地,空氣里彌散著馥郁的棗花香。這時節地里的麥子就開始黃了,日頭散發著白亮亮的光,晃得人睜不開眼,村頭彎脖子柳樹的葉子也蔫蔫地打著卷兒,失去了往日翠綠的俏麗,麥子卻在這樣的天氣里迅速地成熟。
每當此時,沉默的父親就開始在磨刀石上低頭磨月牙樣的鐮刀。每天他都會去麥地里守望。面對著麥田,父親黝黑滄桑的臉上掩飾不住即將豐收的喜悅,像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父親其實只能算半個農民,他在十幾歲就招工去了城里做了建筑工人。那是城里人不愿意干的一項工作,又累又臟。可為了能吃飽飯,也為了能給家里省出一個半大小子的口糧,父親退了學,在奶奶不舍的目光里踏上了去外鄉的路。
后來父親和鄉下的母親結了婚,并陸陸續續有了我們兄弟姐妹。莊稼地里的活兒全靠母親一人支撐著,直到哥哥姐姐能幫上母親。那是多么漫長的一段歲月啊!哥哥姐姐相繼成家以后,母親積勞成疾已經無法從事繁重的莊稼活兒。這時父親申請了病退回家替代母親種地。他之所以能成功的病退下來,也是因為成年累月的腰肌勞損,病痛使他無法再繼續做建筑工的緣故。那年我十二歲。
等某一個天剛麻麻亮的清晨,父親從墻頭上摘下閑暇時搓好的茅草繩,推上木車去麥地。他的身后是睡眼惺忪、磨磨蹭蹭的我。遠處山腰里一層層的梯田閃著豐收的金黃光芒,沉甸甸的麥穗挺著驕傲的腰桿,像接受檢閱的士兵般鋒芒畢露。雖然是靠天吃飯的梯田,卻因了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麥子的長勢并不比水澆地的差。
蟲兒還在地頭淺吟低唱,似乎沒察覺黎明已悄悄到來,麥子在父親的身后卻已經倒下了一片。麥田里混合了山頂柏樹的清香、地里的泥土香、麥桿香還有父親身上的汗味,這應該是收獲的味道吧?我學著父親的樣子,一刀刀割著麥子,麥子隨著“嚓嚓”聲應聲倒地。等紅彤彤的太陽跳上山頭,我們就開始捆麥裝車準備回家了。山路崎嶇難走,滿滿一車的麥秸捆又擋了視線,吃重的木車咯吱咯吱地響著,這讓腰有舊疾的父親舉步維艱。我卯足了勁,把拉車的繩子繃得直直的,麻繩勒進肩里,生疼。我咬著牙硬挺著,心想這樣父親就能推得輕松點吧。
等山前坡后角角落落里的麥子都一刀刀收割完曬在打麥場里,到了日頭最毒的一天,父親套上轆柱開始拉場。我們家沒有拉場的牲口,不像胡同里光珍家有頭得力的小毛驢。麥場只能靠父親套上繩子拉。我在轆柱架的邊上再拴根繩,同父親一起拉。我在外圈,繩子又長,沒幾圈下來就跟不上,父親不說話,只是更用力地蹬緊肩上的繩子,我緊緊地抓牢繩子努力跟上。毒辣辣的太陽正在頭頂,汗珠子摔在地上悠忽一下,瞬間就沒了蹤影……經過十幾天這樣無休止的勞作,等麥秸垛一個個在村莊的周圍堆起來,麥收才算完事。
等我大學畢業后留在了城里,父親一個人更無法侍弄那些莊稼活了。況且他年齡大了又添了肺病,活動一劇烈就喘得厲害,我一再動員,他才和母親進城定了居。
昨天我剛進家門,就發現家里多了兩小袋榮元面粉,一問才知道兩人竟然坐十幾站公交車去大潤發超市買回來的。我按捺不住火氣沖父親大聲地喊:“小區超市什么買不到?跑那么遠去買兩袋面,你們想干什么啊?”父親不急不惱喘著粗氣辯解道:“今天天好,我和恁娘好久不出門了,俺們心思出去活動活動……”看著須發皆白,佝僂著身子的老父親,我猛然一驚,父親是想老家他那一片麥田了吧?
我腦海里悠地閃出這樣的畫面:麥田里金色的麥浪翻滾,獵獵的風吹起父親的衣衫,手拿鐮刀的父親站在麥田里像一位英勇的將軍,滄桑的臉上藏著幸福的希望。心頭那首清越悠長的小調又再次響起,“鼓鼓翅子紅一遍,下來麥子吃涼面,鼓鼓翅子紅兩遍,下來黍子吃炒面,鼓鼓翅子紅三遍,下來谷子吃干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