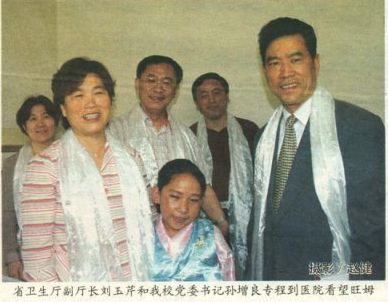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講座

新聞采寫講座 方舒妤/攝

新聞攝影講座付欣怡/攝

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與新聞人才培養討論會

屋前的老人們徐越業/攝

吉祥花覃霜瓊/攝

攔路酒黃柳艷/攝

織布全子孱/攝

歷史街區張柳清/攝

水車莫靜曉/攝

大型浮雕與主碑姚茂朝/攝

新聞卓越班同學參與節目錄制

新聞卓越班同學在梧州電視臺實習

新聞卓越班同學參與《揚帆新時代錦繡新廣西》宣傳拍攝
2001年,上海市委宣傳部與復旦大學合作共建新聞學院的中國特色的新聞學院建設模式,2013年12月,中宣部、教育部在上海召開現場會,決定在全國范圍推廣部校共建模式。2017年4月,全國“部校共建”模式深入推進,梧州市黨委宣傳部與學校共建新聞學院(專業)正式啟動,發揮業界學界各自優勢,打造合作平臺、建立合作機制,走新聞教學與實踐深度融合的新路。
兩年來,“部校共建”極大地促進了我校新聞教育教學改革,取得了顯著育人成效。
卓越新聞人才培養思想保障有力。部校共建之后,在自治區黨委宣傳部的統一安排下,著名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學者鄭保衛教授兩次為新聞學專業的師生作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專題報告,指導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課程的開設。學校開展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讀書征文比賽。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深入人心,有力保障了卓越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
辦學條件明顯提升。兩年來,建成了融媒體中心,購置了攝像機5臺、單反相機20臺、無人機2臺、專業圖書10000多冊。通過“千人計劃”實現了媒體人員和新聞學專業教師的雙向流動,媒體資深記者邱潔玲、知名主播馮宇紅、陳文靜走進課堂,為同學們精彩開講。通過到媒體掛職鍛煉,專業教師充實了媒體從業經驗。
學生實踐機會更豐富。在用好院報、院網、院廣播電臺、學校官微等院內媒體的基礎上,借助部校共建的契機,開拓了梧州日報社、梧州廣播電視臺等校外媒體實踐基地,特別是梧州日報社的“融媒小廚”,代表了媒體融合的發展方向,能夠為學生提30多個的實習機會。14、15級同學,先后到柳州三江、桂林興安開展校外新聞綜合實踐,并將實踐成果結集。課程的實踐扎實開展,如依托《媒介素養》課程,開展了“媒介素養進社區、進校園”系列活動,并得到梧州電視臺的關注報道。
卓越新聞人才培養取得階段性成果,兩年來,梁媛媛、范煜奇等9位同學考上廣西大學、南昌大學等知名高校碩士研究生。學生社團活動、專業競賽、沙龍座談蓬勃開展,返屋企民俗學社開展的傳統文化傳承活動富有特色,已經成為學生社團中的佼佼者。大學生通訊社培養了一批宣傳骨干。第一期新聞卓越人才班20名同學結業。兩年來,新聞學專業學生在光明網、廣西日報等等各類各級媒體上公開發表的稿件和文章超過400篇,獲得全國性獎勵10多人次。
未來,我們將深化“部校共建”,定不辱使命。文/朱俊海
2014級新聞班篇
侗族姑娘,誰為你做的嫁衣?
謝東洪 楊舒婷每年春節,婚禮的氛圍都會在程陽八寨的上空氤氳著,待嫁的新娘隨身而攜的幾十套手工嫁妝,也會在熱熱鬧鬧地歡呼聲中被抬進夫家······走在巖寨中,隨處可見高高的木架上飄揚著青黑色的侗布,這些半成品的侗布,就是侗族姑娘嫁衣的初形態。
層巒疊嶂的異常閉塞,逼迫著侗鄉兒女們依舊保持著自給自足的農耕形態:房梁上懸掛著來不及吃的、腌制了一年的肉類;正在建造的居所,材料便是山上的原木;就連遮羞蔽體的衣物,也必須從種棉花開始、紡紗織布后裁剪而得。
而侗族姑娘正是在這樣閉塞的環境中,練就了一身本領:自己做嫁妝。
現年39歲的陳群麗,經營著一家賣侗族手工發飾的攤子,女兒在不遠的鎮上念高中。盡管距離女兒出嫁還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但是她早早地就已經開始為女兒準備了嫁妝。陳群麗從自己母親那里收到的嫁妝還有十幾套沒穿過,她估摸著這幾年再做幾套,湊足二十套嫁妝之后,就可以開開心心地送女兒出嫁了。然而,制作嫁妝的難度不小,對本身就不太會的陳群麗更是難上加難。
制作嫁妝,首先要從種植棉花開始。這是嫁妝制作的第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侗族人不太會將此項工作假手于人,購買市面上的棉花以獲取便利,因為在他們的觀念里,這樣的做法根本不能保證布匹成品是否是純棉材質。
接著便是紡紗。紡紗是一門技術活,右手執棉,左手搖動著紡紗機,均勻地將棉花一點一點紡成紗線,而不耐心的制作者,就會將紗線紡得一節細一節粗,完全不合要求。
然后在織布機“啪”的操作聲中,緊實、潔白的棉布就被一段一段地織出來了。效率高的織者,一天也就才能織出5米左右的布匹,但是完整的一套嫁妝里面可包含了幾十件衣褲!
最艱難的持久戰就要來了:染布。侗族婦女們常常會采摘自己種植的藍靛草(侗族人通常稱為“藍草”,取其侗語發音“Ian”),將一匹寬約一尺,長三四丈的白布料,放到藍靛桶里浸泡。數小時后,拿到河邊清洗、曬干。這樣反復3-5次后,一個夏天的時間里,布料由白變藍,由藍變成青黑色。染布過程中,婦女們基本干不了什么活,必須掐著時間點趕到染缸旁守候著。藍靛草在侗族文化里有辟邪的意思,婦女們用藍靛草染布,也是為了將幸運穿在身上,隔離邪氣。
接著再漿上薯莨、牛皮膠,然后用甑子熏蒸,布料慢慢變成紫色。最后在平滑的青石板上用木槌反復捶打,使布料由粗變平,由厚變薄,由紫紅繼而發亮。生生不息的捶打聲是侗布即將完成的信號聲,量體裁剪后,一件嫁妝宣告完成。而幾年以后,整套包含了20件衣服以上、大約5條褲子和5雙繡花鞋的嫁妝的制作才正式落下帷幕。
2015級新聞班篇
如果你沒法阻止戰爭,那你就把真相告訴世界丘傳龍這是一句戰地記者的格言,也是我這次采風后最深的悸動。
2018年10月13日,15新聞班在老師的帶領下參觀了位于廣西桂林興安的湘江紀念館,走黨史,考察紅軍長征路,并在講解員的講解下對湘江戰役有了更深的認識。它不僅是紅軍長征途中規模最浩大、鏖戰最激烈、傷亡最嚴重、場面最慘烈的戰斗,而且在人民軍隊近90年的戰爭史上,乃至現代世界戰爭史上,其殘酷性、慘烈性能夠與之相比的,也屈指可數。原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炮兵政委、紅軍詩人陳靖在《黔山湘江》一詩中寫道:“血染十里溪,三年不食湘江魚,尸體遍江底。”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紅軍在湘江上游廣西境內的興安縣、全州縣、灌陽縣,與國民黨軍苦戰五晝夜,最終從全州、興安之間強渡湘江,突破了國民黨軍的第四道封鎖線,粉碎了蔣介石圍殲中央紅軍于湘江以東的企圖。
湘江戰役是中央紅軍突圍以來最壯烈、最關鍵的一仗,我軍與優勢之敵苦戰,終于撕開了敵重兵設防的封鎖線,粉碎了蔣介石圍殲紅軍于湘江以東的企圖。紅軍雖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鎖線,但付出了巨大的代價。5軍團和在長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國際師損失過半,8軍團損失更為慘重,34師被敵人重重包圍,全體指戰員浴血奮戰,直到彈盡糧絕,絕大部分同志壯烈犧牲。渡過湘江后,中央紅軍和軍委兩縱隊,已由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人。
在紀念館中全體黨員走進湘江戰役紀念館,同學們認真觀看了館內展出的一件件物品,陳列出的陣亡戰士名單,重現的每一條戰爭路線。有人駐足展覽館中一些珍貴的圖片資料前,拿出手機拍張照片,留下這難忘的一刻;有人目光停留在展柜的珍貴文物上,體會革命年代的艱苦歲月。一個多小時的參觀,我們進一步了解了湘江戰役的歷史,并深刻感受到了我黨革命先烈為革命的勝利展現出的不怕犧牲的崇高精神。
而我更為感觸的是,這些歷史資料,相片等都是被活著的軍人或者他們的后代記錄下來的,我不知道那時候是否已經有了戰地記者,可能這些就是戰地記者用生命留下來的財產……作為一名新聞專業的學生,通過三年的學習,尤其是對“新聞學”這門課的學習,我慢慢的對記者這個職業有了更深的理解,對如何成為一名優秀記者有了一些的感悟。
“戰地記者”,對于生長在和平時代的我們似乎是一個很遙遠的職業,從事這個工作意味著遠赴他鄉、整天生活在戰火硝煙的危險下,通訊受到限制,不能洗澡……“如果你沒法阻止戰爭,那你就把戰爭的真相告訴世界”,這是戰地記者永遠的格言。這是一群與死神經常擦肩而過的人,也是一群與戰爭無關的局外人,他們冒險、沖動、熱情,充滿責任感,他們的工作就是力爭在被不可預料的槍擊、炸彈、導彈或地雷奪去生命之前,用文字、聲音或圖像將戰爭記錄下來,向世界真實傳遞著戰..............無論是在世界大戰的巨型舞臺上,還是在局部戰爭的彌漫硝煙中,最及時、最生動、最忠實地將戰爭實況報告給渴望真相的千千萬萬公眾的,不是軍方信使,不是一-般作家,不是歷史學家,而是這些置身于槍林彈雨之中、以生命為賭本、去攝錄戰爭場面的特殊的新聞人一一-戰地記者。向戰地記者至于最崇高的敬意!
卓越班篇
美是辛苦的勞漢燕在很多人看來,美的形式有很多種,比如,美有規則的美,整齊的美,凌亂的美,還有幾何的美,而現在許多城市的公園,路邊的美化,都要講究一種對稱美,整齊美,和幾何的美感,花草必須修的整整齊齊,一種幾何的美感撲面而來,但是讓人感覺有一點單一,而花壇中的草,和綠化的草里都不允許有雜草混合,生怕破壞了那整齊的美感。
現在城市的綠化用得都是同一種名為草坪草的草,它是一種觀賞類的草,這種草現在在城市里被廣泛使用,而玫瑰湖公園的草就是這種草,但是有泥土的地方就會有雜草,雜草的生命力是頑強的,它在泥土中和草坪草相伴而生,但是人們為了美觀就必須將草坪草中的雜草去除,但雜草和草坪草相伴而生,根系相互交錯,極難去除,它需要除草工人用一把小鏟子用力的鏟下去,將泥土翻滾起來,然后用手一點一點將兩種,甚至三種以上的草努力的分離出來,這種工作是需要耐心的,因為這個工作是極其耗費時間的。一天之內,工人也去除不了多少。
而梧州市地處中國的南方,處于亞熱帶季風氣候區,雨熱同期,草類的生長也是極其繁盛的,一小塊的綠化草坪中可以混雜著多種的雜草,而去除雜草的工作又是極其耗時間的,當游人在游覽公園的時候,游人看到的整齊,單一,沒有一絲雜草的草坪草的時候,背后是除草工人努力的體現,美不是與生俱來的,它是需要人創造的,美同樣不是容易的,它是工人們一點一點用手分離出來的,是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