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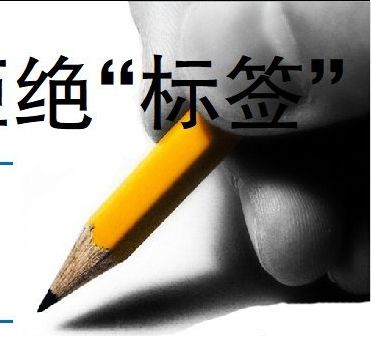





據紅網報道,教育部日前召開新聞發布會,介紹2018年教育事業發展有關情況。教育部表示,我國已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高等教育體系,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48.1%,我國即將由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進入普及化階段,但公眾和媒體“標簽化”大學生的現象還很普遍。所謂“標簽化”,就是預設“大學生本該如何如何”的隱喻。
“標簽”指某物被定型化或者被歸入某一類,而不是將其視為一個獨特的個體。那么,何為“教育標簽化”?“教育標簽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大學生專業強加定式,大學生作為社會上備受關注的一個群體,很容易被“標簽化”。隨著我國高等教育體系不斷發展壯大,大學生比重增加,但公眾和媒體對大學生的專業定式也隨之而來。認為畢業后就業必須與所學專業對口;二是給大學生分三六九等。普及化、平民化的高等教育,本意是“以教育權的平等化實現人的發展機會平等”。而近些年來,隨著“高等教育精英化光環”的逐漸褪去,社會上一些公司有一股“重新給大學生分等級”的苗頭。
所謂重點大學VS一般大學、所謂研究型大學生VS職教學生,似乎大學之間有高低之分,大學生之間有等級之別,這是對高等教育的曲解,高等教育應該是給任何可能個體適合的教育,發展其身上的潛能,開啟通向未來的路口,而不是給人貼上高低貴賤的靜態標簽。高校之間只有類型分工之別,不該有上中下之分。 “‘標簽化’大學生是一種
隨著我國教育體系的不斷完善,近年來涌現出了許多新型的教育理念。比如,對于學校的辦學理念,有的叫“生命教育”,有的叫“小公民教育”,有的叫“尊重教育”,可謂是多種多樣;對于學校的文化,可能是受所謂的“一校一品”的學校文化建設思路的啟迪,有的學校致力于打造“雅文化”,有的致力于打造“家文化”,盲目樹立概念,將會局限學生的專業選擇。
“‘術’應當是廣泛學習,而不是僅限于自己的專業。作為當代大學生,我們應該博學,不要讓任何人給專業下‘標簽’。“我們這一代大學生正處于新時代,需要我們一起創造美好的未來。我認為‘標簽’只是其他人給我們的設定,更重要的是我們自己不能被‘標簽’限制,社會公眾給我們設定的標簽并非惡意,只不過他們不能完全了解大學生。我還是希望社會能夠重視對大學、大學專業的宣傳,從整體出發,改變公眾觀點。”我院傳媒學部廣告學專業2018級紀冉這樣說。特色創建活動可以說是這些年教育界的一股潮流,其初衷是好的,是想改變原來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千校一面的教育現象,努力增加和凸顯各校、各科
社會在普及高校教育的同時,也應大力宣傳高校的不同功能,普及術業有專攻的基本常識,學術氛圍的發展,不應當越來越局限,保持專業特色化的同時,也要注重學術多元化的發展。學校也應加強宣傳,運用現代科學技術將自身學校的功能詳細完備的介紹給社會公眾,從而減輕社會公眾對高校大學生“標簽化”的影響。公眾也應意識到在高等教育普及的現今,大學生選擇職業類型多樣化。只要在自己的崗位上發揮自身價值優勢,對于社會來講就是有意義的。因此社會大眾應以包容的態度對待當今各高校大學生,而不是站在大學生的對立面指責大學生的選擇。
大學生自身在大學生活中盡自己所能的學習專業知識,在大學生活里鍛煉自身能力,從而提高自己的綜合能力。步入社會進行工作時發揮優勢,其次,大學生在選擇工作時要將社會利益放在首位,為社會貢獻自己的價值。改變教育體系結構,仍有許多尚待解決的問題,解決的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全社會的共同改變。“我認為首先國家政府對社會大眾的引導很重要,其次當今時代的信息傳播速度很快,報紙網絡的輿論引導也很重要,最后學校也應有專業的對外交流部門來解釋自己學校的功能。當然大學生的自身努力也是必不可缺的。四方共同努力解決大學生‘標簽化’的現象。”我院文學部漢語言文學專業2018
“去標簽化”帶來一種不太合理的大眾思維。在我國,學歷和就業之間存在一種隱性的對應關系———所謂高學歷就要對應光鮮的有面子的職業。而實際上,求學、就業應該是個體個性化的選擇,而不是按固定模式成長。在高等教育大眾化的背景下,如果只關注大學生身份,高等教育規模持續擴大快速地滿足這種“身份需求”,會使不少人空有大學生身份,卻沒有實質能力,既讓大學生對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也會使整個社會迷失在“身份教育”中。
社會群體對于大學生形成的思維慣式對大學生就業有很大的影響,其一是因為社會群體對于大學生的包容性較低,認為大學生在接受過大學教育后理應為社會做出貢獻。因此在大學生想要自主創業或從事自由職業時,部分人對此不能理解,甚至對大學生進行勸阻。這就使大學生在就業時考慮的問題增多,找工作變得束手束腳會嚴重的影響大學生的發展前景。不同大學之間的功能分工不同,因而承擔的社會作用也不同。大學生不應被他人貼的“標簽”束縛,要認清自己的水平和能力,理性選擇適合自己的社會身份。“讓大眾了解大學生的學習,理解大學生的知識深度,增加大學生活與社會的聯系,使大學生活更加透明化。”我院文學部漢語言文學專業





